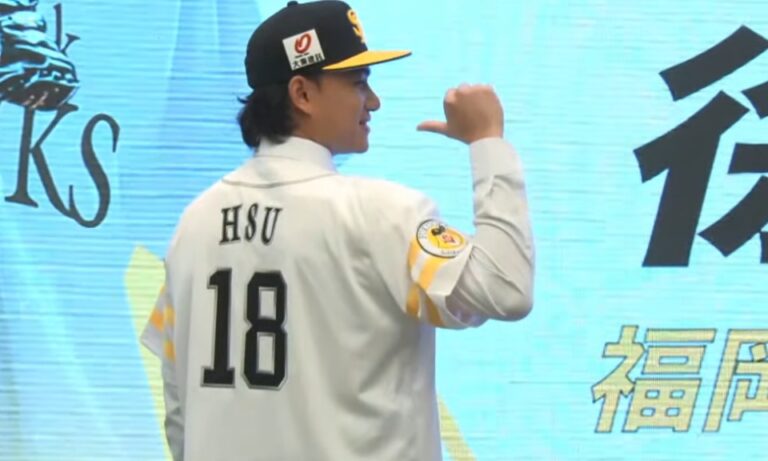每年7、8月是花蓮地區的祭典高峰期,各部落年祭也有不同稱呼,無論是Ilisin、Cipoo’、Malalikid、Kiloma’an或是Qataban,各部落都會以在地的方式進行年祭儀式,這也是部落族人們與祖靈相聚的時刻,幾乎旅外族人都會返鄉共襄盛舉,堪比農曆過年的熱鬧氣氛。
族人手牽著手、圍成同心圓齊唱著祭歌,沉浸在這個相聚時刻;但是有族人發現到,當代的參與人數跟過去有些微落差,而且在族語能力出現明顯斷層,部分原因跟孩子們的成長經歷有關連。
‘Okakay(大興部落)豐年祭大會會長 Oneng Falahan(陳真華):「你說他認不認同族群身分,我還覺得阿嬤帶的小孩子比較認同這個文化的部分,你說如果他跟著爸爸一起去都市打拚,可是久而久之環境變了、他很多事情都忘了,因為從小沒有養成跟著部落一起共事,比如豐年祭的部分,如果他從小沒有接觸
長大以後,更沒有自信參加祭典這個部分。」
此外在年祭前夕,部落也會有祭場周邊布置、祖靈屋搭建或是年齡階層教育訓練等的許多的環節要完成,而考量人數問題,只能在周末假日期間要求青年們回來把握時間趕工,也讓各階層負責領導管理的級長們非常困擾,讓文化永續陷入困境。
Tafalong(太巴塱部落)Lapalo’階層級長 Ka’ti’ Rake(林楷倫):「還是要強調常回來看看自己的部落,因為現在少子化的關係,階層人數也越來越少傳承這個東西,其實很難,沒有人也不知道要傳給誰,我們現在目前碰到的危機就是人數的問題。」
Kiwit(奇美部落)Lakacaw階層級長 Talod Tamod(蔡孟帆):「還滿疲憊的,因為回來時間很久,像我自己回來就將近有一個月,睡覺的時候會想工作進度,因為怕有些事情還沒有忙完或者是來不及,希望更多年輕人回來一起參與、一起幫忙。」
除了每年8月年祭之外,7月是奇美部落進行男子技能訓練的期間,也就是所謂的Komolis(捕魚祭),目前擔任前置作業執行任務的青年也提到,即使有三天歲時祭儀假也不夠用,只能自己設法在文化傳承跟當代社會的拉扯中,取得平衡點。
Kiwit(奇美部落)Lakacaw階層青年 Calaw(高振偉):「Tokolo(第3級)跟Adawan(第4級)應該是監督跟尋找材料的部分為主,可是現在變成說人員配置跟以前不太一樣,變成說Adawan要全部都下去一起幫忙工作,因為畢竟人很少,也不可能等學生都放暑假才開始籌備,這樣子會來不及,我覺得這是目前很大的問題。」
由於部落人口外移嚴重,而都會區環境的也改變新世代族人的價值觀,耆老則認為語言隔閡、成長歷程改變及部落經驗不足等因素是導致祭典參與人數下降的原因;因此從家庭教育著手提升族群認同並且鼓勵孩子們返鄉參與祭典,搭配適當誘因,也許是扭轉目前各部落傳承危機的重要關鍵。
‘Okakay(大興部落)豐年祭大會會長 Oneng Falahan(陳真華):「只要你是原住民的小孩,只要你是部落的小孩,最好是能夠認同你是原住民,所以我剛剛有講過一句話,就是我們要有自信,我們要把我們的心放在部落,然後旅外工作沒關係,只要初衷在部落那就好了。」
責任編輯:黃金倪